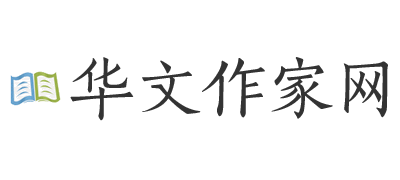葉彌可能就是本雅明所懷念的那個“講故事的人”,這其實是面對毛茸茸的歷史圖景和盤根錯節的故事紋路,而采用的一種不引導、不歸納、不扭曲的“虛構”態度,借用萊昂內爾·特里林的說法,這態度非常“誠與真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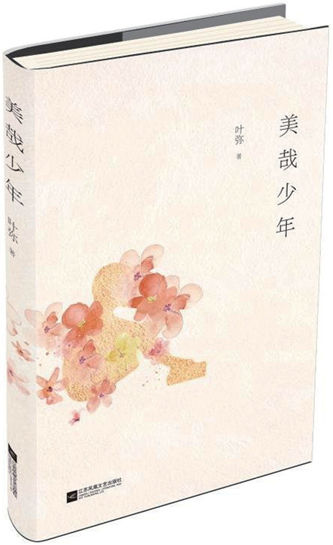
情欲充盈的時刻,革命從天而降,這是葉彌長篇小說《風流圖卷》里的一個場景。歡愉滋生得如此自然,如同“滿街的白蘭花開著”,暴力雖迅疾粗暴,但是也有山雨欲來的提醒。于是,這個暴力和欲望并置的場景便有了多重意味。革命與暴力絞殺了情欲,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看法。在大多數類似的場景中,讀者會習慣性地將愛情、身體、歡樂與革命、暴力、禁欲對立起來,認為兩者在同一語境下水火不容。前者的存在是為了批判、控訴后者,進而達到對作為總體的某段歷史及其意義的消解和否定。后者亦常常被簡化為非人化、非意志化的機械性力量,它要么被別人操控要么操控別人,從而有目的地或者盲目地摧毀、拆解后者。“革命”與“機器”這兩個詞匯組合成“革命機器”這個常用詞,大約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。“革命絞肉機”無非是更為極端的說法。
很顯然,葉彌不愿止步于此。不過這已經顯示了葉彌在處理類似主題時的與眾不同。葉彌從1958年和1968年這兩個敏感的歷史節點開始講述這些故事。前者往往與反右、大躍進等重大歷史事件產生聯系,后者則涉及“文革”爆發、武斗席卷全國、軍管城市等不同階段。重大的歷史時刻接踵而至,革命的熱情和實踐亦逐步升級。然而,在集體性創傷冷靜鋪展的同時,情愛故事卻依然搖曳生輝,權力、性、暴力、倫理之間盤根錯節地纏繞在一起。于是,故事里彌漫著奇妙而曖昧的氛圍:革命機器發出的巨大轟鳴聲中不時傳出情欲的低沉吶喊聲。與其說這里傳達出的是關于反抗的意義和隱喻,倒不如說,革命更像是催化劑,反倒激發出欲望、倫理,表現出更豐富的層次和意義形態。
葉彌試圖描述的故事和觀念大約是:或許歷史的表情本就沒那么僵化,情欲和革命本都是構成歷史的“自然”因素,皆在大歷史的紋理、肌質中生長、蔓延。為了爭奪歷史的陽光和水分而相互抵抗、消解其實只是其中的一種面相。刻意去尋找扭曲或毀滅故事的眼睛,大約會忽略歷史的其他表情。在歷史的暗夜中,它們未必就一定是相互仇視,可能是互不理睬,也可能是相互啟發甚至是相互掩護。說到底,歷史的真相不止一種,隱藏的手段亦多樣,革命時期的情欲到底是禁忌和反抗策略,還是歡愉和享受,又如何分得清楚呢?葉彌如此對待情欲和歷史,難免會讓人聯想到王小波。很顯然,后者更樂于在兩者之間設置一個怒目金剛的視角,采取一種更加直接的短兵相接的敘述策略。只是在一個不談革命、懶得革命的泛娛樂時代里,王小波被人重新提起時,只剩下了空空蕩蕩的性,至于與性相關的歷史則被毫無耐心地忽略了。葉彌的意圖和實踐或許還有值得商榷之處,但是她至少做到了一點:革命與情欲相遇的時刻里,他們的表情都是豐富的、意味深長的。這倒是印證了哈羅德·布魯姆的一個觀點:“我們讀她,是為了人物,為了故事,為了形而上學的省思和情欲的省思,以及為了某種帶反諷的處世哲學。”
葉彌并非突發奇想,刻意展示革命中的情色表演。在葉彌的觀念里,革命年代里的故事不是只有悲情和血淚,革命本身也并非時刻都青面獠牙。那些有柔韌性的故事本身的光彩足以照亮暗夜里的某段路程,在這些時刻革命會顯現其不易覺察的懈怠、脆弱、疲倦,革命虛弱的瞬間甚至會讓人覺得竟有了溫度和倫理。《美哉少年》便是這樣的故事,不妨把它視為《風流圖卷》的前傳來讀。
小說的第一章,作者描述了李夢安和妻子朱雪琴這“一對特別沉得住氣的夫妻”的日常生活。“李夢安拿出他的《毛澤東選集》躺倒床上去看,他在書里夾了一本薄薄的《黃培英毛線編織法》,一九三八年出版,封面上套印著當時的電影明星周璇穿著毛線衣的照片,眼睛向下斜睨,作望穿秋水狀。”“朱雪琴今天的目標是照著菜譜做一道藥膳‘西瓜雞’,她拿起她那本《毛澤東選集》進了廚房……原來她在選集里夾了一本手抄的菜譜。”“朱雪琴拿著勺子不經意地敲著李夢安的腿,勺子和腿共同制造出來的聲音讓她感到心里很安穩,那聲音是結結實實的。”這個革命時期的日常場景,包含了諸多龐雜而又極富意味的信息,它們可能為理論的介入提供了較好的例證,但是如何掌握闡釋的限度也是需要考慮的。因為這些經驗的魅力恰恰來自于各種意味微妙地融合、平衡、牽制而形成的張力,而非某種單調的傾向和形態。
《毛澤東選集》蓋住了畫冊和菜譜,意味著革命對審美、日常秩序的否定和壓制。坦率地說,這樣的理解是政治非常正確的陳詞濫調。事實上,把這樣的細節僅僅理解為對故事發生語境的提醒,也未嘗不可。反之,也可以把選擇《毛澤東選集》作為封皮隱藏畫冊和菜譜理解為主動行為,這便意味著群眾通過陽奉陰違的方式消解了革命的意義、抵制了革命的改造,從而最大程度的保全了日常。這似乎為巴迪歐所說的“群眾沉默的威力”提供了絕佳的案例:“這是特殊惰性的威力”,是“吸收和抵消的威力,這種威力從此以后遠遠高于施行于群眾之上的威力”。巴迪歐對“在沉默大多數”所造成的“陰影”效果有過經典描述:“退縮在私人生活中完全可以成為對政治事務的直接挑戰,這是針對政治操縱的積極抵抗形式。角色顛倒過來:正是生活的平庸,正是日常的生活,即人們曾經譴責的小市民的東西,那些卑賤的非政治(包括性欲),他們成了重大時刻,而歷史和政治事務則在別處展現他們那抽象性的意義。”不可否認,這樣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,我并不認為葉彌描述這個場景,只是為了積心處慮制造一個精妙的隱喻效果。巴迪歐理論發生的原始語境與中國革命具體情況的差別,是需要稍加注意的。百年來歷次的革命動員中,基本的共同體意識幾乎從未在群眾中建立起來,比起群眾的公共關懷和政治介入,恐怕更多的還是魯迅所言的“做戲的虛無黨”,在這里很難區分所謂的積極和消極的意義抵抗。而在革命的間隙或者革命出現倦態時,“敷衍革命”的背后恐怕還是樸素、頑強而又極具包容性的中國特色的生存意識。
當妻子用勺子輕輕敲打丈夫的腿時,“食”與“色”的碰撞發出了“結結實實”、讓內心“安穩”的聲音,自然而又葆有意味和力量的精妙隱喻在這里誕生了,而此時“革命”真的在別處,淡淡的情欲開始升起,它同其他細節一樣都在為隱喻的誕生做鋪墊,然而暫時的滿足背后卻是關于未來的惶恐,因為“革命”其實并沒走遠,于是這個場景又多了一重意味。葉彌是洞悉這一切的,所以她才要盡可能而又極簡地將其呈現出來,她最大的努力也是不讓任何一種意味成為主導氛圍的因素,而破壞了一幅信息凝練而意蘊駁雜的畫面。正是在這一點上,葉彌可能就是本雅明所懷念的那個“講故事的人”:“故事不耗散自己,故事保持并凝聚活力,時過境遷仍能發揮其潛力。”說到底,這其實是面對毛茸茸的歷史圖景和盤根錯節的故事紋路,而采用的一種不引導、不歸納、不扭曲的“虛構”態度,借用萊昂內爾·特里林的說法,這態度非常“誠與真”。